
10月24日,在上海思南公館,作家路明圍繞著自己的新書《出小鎮記》,和蘇更生、景蠻蠻一起,向現場觀眾講述了小鎮和上海的故事。

路明:我媽媽是69屆的初中生,他們69屆那些人走的時候,69屆是一片紅,就是那一屆初中和高中的畢業生沒有一個留滬的指標,當時1968年有一個通告知識青年要下鄉接受教育非常有必要,之后69屆就是一片紅,當時插隊的地方是臨時換到了彭浦站上車,當時凡是去過縣城的人,有一個細節非常難忘,一開始大家過去送,會講一些豪言壯語,但是等到火車一開,因為老式火車動的時候,先是往后退一退,然后再往前開,火車動的時候,突然之間一下子控制不住整個場面,哭聲震天。
當時等于在車上車下所有人一起哭,哭聲可以傳出好遠,我后來也會采訪當時的知青,他們說他們在貨車上本來很樂觀,想好是不哭的,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,你會受感染會哭,一直要哭到黃渡,才會停下來,停下來之后,因為那些都是18、19歲的少年,大家又開始嘻嘻哈哈的,又把自己各自背包里面的面包、撲克牌拿出來,之后你要看到底坐到什么地方。我采訪的有些知青,像我媽媽當時去安徽算是比較近的,火車坐了一天一夜,坐到黑龍江是要坐三天,最遠要去云南南倉縣,需要做三天三夜的火車,而且是做知青專列,接下來從昆明到南倉坐卡車要坐五天,到了南倉縣再去插隊的地方還要再走一天,之后就會想象,可能是1978年之后,對于上海知青來說,他們心中的上海,除了有他們兒時的記憶,很多人也會特別銘記當時在上海火車站送別的那一刻。
所以我覺得對于父母來講,無論到什么地方,他們都認準了我就是上海人,他們一有機會就要講上海話。

路明
景蠻蠻:我很好奇你已經成功考回上海,落戶在上海,變成了新上海人,之后你媽媽是如釋重負嗎?她是什么感情,以及她對小鎮有沒有新的東西?
路明:我媽媽對小鎮應該是沒有太深的感情,對我媽媽那一代上海人來說,小鎮對于他們來說就像一個車站一樣,我在這邊暫時停一停,停多久不知道,但是將來一定會回上海。
對于我們來說就會比較矛盾,在家里面聽父母說要回上海,但是同時你從小就生活在這里,你最好的小伙伴都是在這個小鎮上,我自己16歲之前很多記憶都是在小鎮上,這些記憶對我來說現在是非常珍貴的財富,所以我才會一次又一次想到我兒時生活的圖景,才會把這些故事寫下來。

景蠻蠻:我能理解路老師的矛盾感,其實我也看過一本書寫我們四川童年的書,很輕快,很開心,我看到它我也會想到我的小時候,但是我覺得你書寫的童年里面的色彩是很多的,比較復雜,蘇老師怎么看他們的區別?
蘇更生:我在看路老師的書的時候在想,上海到底有什么魔力讓大家這么念茲在茲,以及你所描寫的從上海來的、渴望去上海的人,他們身上表現的倔強跟別人不一樣,我會好奇。
路明:其實我從小也很困惑。
蘇更生:那現在你作為一個新上海人,你媽媽回上海了嗎?
路明:回上海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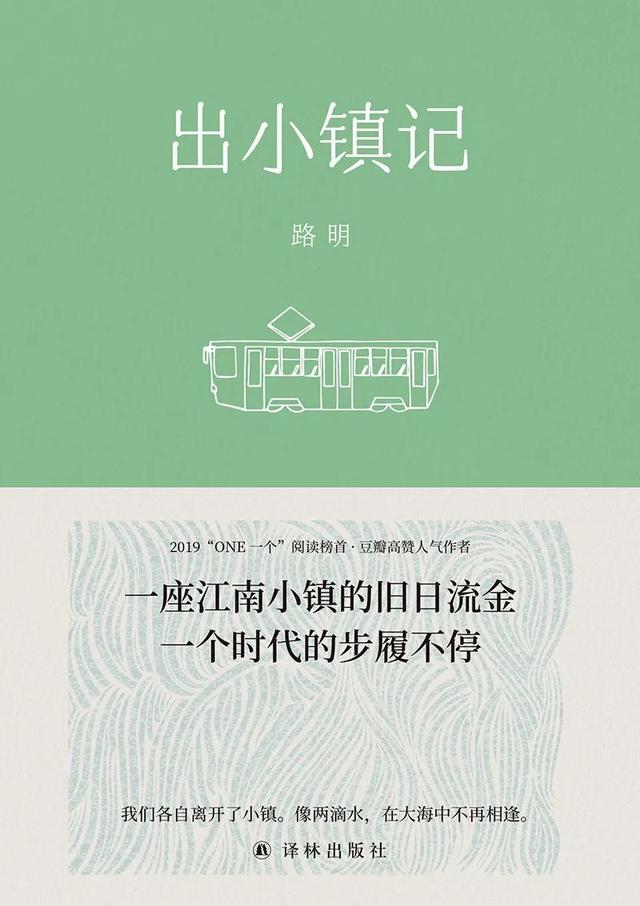
蘇更生:在終于心愿得成回到上海之后,你們的感受是什么,我就要呆在這里一輩子再也不走了,或者說它并不是我小時候期待的摩登的大上海?
路明:我先說我自己,離開小鎮回到上海,我挺舍不得的,因為我初中的時候暗戀一個姑娘,她當時考取了昆山的中學,而我當時就來到了上海。有一陣我也沒有覺得上海有多么好,哪怕在我小時候,其實很多時候是我的媽媽她催我說你最近有沒有空,到上海去看看外婆,我心里面并不是很情愿,第一個原因可能在于路上真的很久,我們小鎮已經算離上海非常近了,我們要坐一輛長途車,有一個小時左右,從安亭到普陀區又要兩個小時,到普陀區還要再坐40分鐘的車,兩天來回就要花12個小時在路上。路上那么辛苦,好像到外婆家也沒有什么好玩的東西,那個時候和爸爸媽媽只能在地上鋪個地鋪。
對于我來講還是更加懷念鄉下的廣闊天地,特別是每年的春節,因為當時我爸是小鎮上的居民,我媽媽嫁給我爸的時候,他們有一個協議:我會要求每年過春節你要陪我一起回上海過。所以每年過春節的時候,大概要在上海外婆家過十天,一開始肯定很興奮,會想到我會吃到小鎮上吃不到的美食,但是往往一過幾天就會很厭倦,最后要數著日子盼什么時候回去,日子越到頭我媽的臉色就會越難看,我們一般是在下午走,上午我媽一定會哭一場然后再坐車回小鎮。
90年代的時候,過了春節之后,空氣還是比較陰冷的,那種氣氛下,長途汽車往小鎮開。很多次我看到我媽一路是哭回去的,但是真的來到小鎮上也習慣了,也沒有想象中那么苦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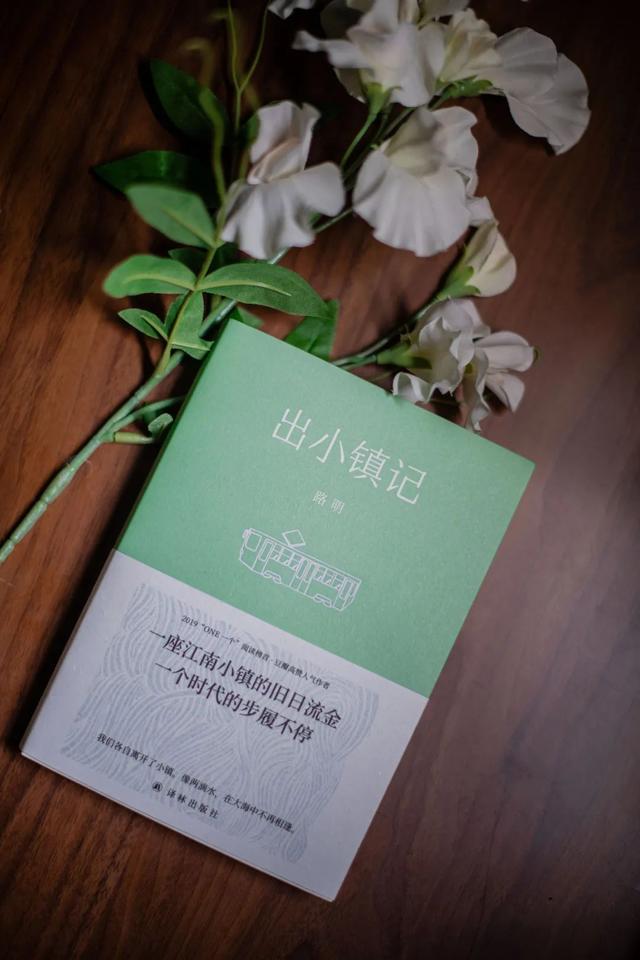
蘇更生:我覺得這個挺有意思的,因為路老師的外婆特別有意思,除了他們要回上海過年之外,他的外婆也會去小鎮去看他們。外婆去看自己的女兒從來不住在女兒家,要住在招待所,自己帶床單的,他的外婆還會學一下昆山的方言,帶一些大白兔奶糖發給四周的鄰居。
我不知道從80、90年代所謂的上海人的形象,我覺得你的外婆就非常非常的上海人的形象,自己帶床單、枕套,你眼中看到的三代、四代上海人,他們有什么變化嗎?包括這些喜歡上海、來到上海的外地人,他們跟你外婆那一代的上海人有什么不同嗎?
路明:我外婆跟我媽還有我,我們三個人是完全不一樣的,我外婆就是根深蒂固的老上海,她對上海的感情永遠比不上我媽,因為她沒有離開過,我媽在他們青春最好的年齡離開了上海,這是他們心頭的朱砂痣。因為當時很多事情對她來說是求之不得的,她對上海有非常深的情感。
她回上海是在她退休之后,因為那個時候有政策了。這個事情挺好笑的,我媽當時在小鎮,很多時候在想,雖然說希望有一天回到上海,他們能做的事情就是要把我送到上海。接下來很多年之后政策又有了一些新的說法,如果說是在外地的知青,你有子女在上海,你可以去投奔他,我媽當時憤憤不平,憑什么我是投奔他。
蘇更生:你身上上海的氣質是什么?
路明:我身上的上海氣質很少了。
蘇更生:那你的小孩呢?
路明:我估計他又會回到像我外婆一樣,他可能就會默認上海就是在他家附近的幾條弄堂。
蘇更生:相當于這一百年中間白過了。
路明:對,就像我寫文章用過一個詞,就是接力洄游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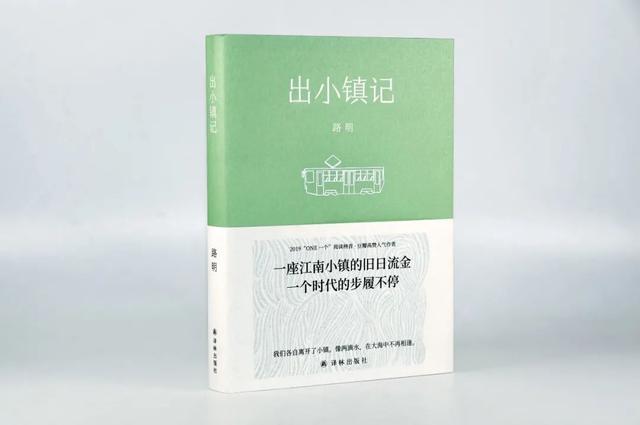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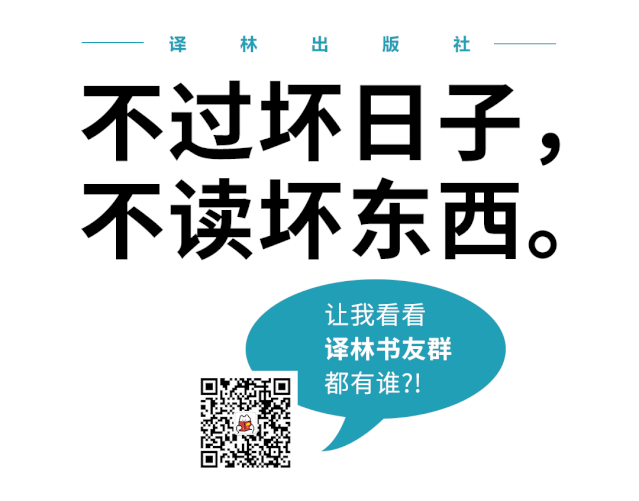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)







慢得多.為什么?)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