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這是頭哥侃碼的第263篇原創
國慶假期回來,「頭哥嘮 B 嘮」的直播仍在繼續。
這次我邀請了我工作上的老板和朋友,一起聊了聊關于 “技術創業路上的苦與樂”。

熟悉他們兩位的都知道,可以說是技術出身,然后創業當老板的代表。
大家都知道,現在國內技術圈很多大佬在這幾年紛紛開始創業,而且都還做得不錯。在外人眼里,他們會覺得“你們融資拿了那么多錢”、“自己說了算想干什么干什么”這種光鮮之詞。
我以前也會有這種看法,但我在支流科技和 APISIX 開源社區摸爬滾打了這一年多之后,現實情況完全顛覆了我的認知。其實這些技術大佬們也沒有想象中的開心。
今天這篇文章的內容主要來源于這次在線直播時的一些討論內容,從三個人不同的經歷背景去聊了聊這些話題,這些東西都是基于我們自己的認知進行描述的,所以不帶有任何的群體色彩,完全都是個人想法。
1
對“技術自大狂”來說,打工與創業之間最大的差別是什么?
溫銘和一樂都是我很早以前認識的朋友,兩位技術大佬都做過一些很牛逼的項目和產品,但從我個人角度來看,大家也看過我寫的一些文章。
就我自己覺得可能很多做技術的同學其實都是自大狂,都覺得自己很牛逼,然后略帶一些旁若無人的感覺。但是你會發現,在創業的時候,可能你對客戶或者對團隊就需要收斂這些風格了。
一樂覺得,位置的變化讓他對自己和對其他人的要求不一樣了。
從我個人角度來看,技術人員從打工切換到自主創業后,最大的區別就是沒有 KPI 了,就好像沒人給你定規矩了。
但這其實并不是一件好事。很多人覺得沒有 KPI 就可以想做啥做啥了,但實際上 KPI 是技術人員在驗證自己收獲或者能力的一個有力保障。因為公司要按照這個 KPI 的完成度來發獎金啊。
只要能按時完成 KPI,剩下的時間都是自己的,想干嘛干嘛。所以 KPI 根本不是限制,而是釋放。
但是創業了就不一樣了,創業了沒人給你定 KPI,你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,也不知道未來的挑戰在哪里。所以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地摸索著,然后試著給自己定一個 KPI。創業場景下,很多時候都是自己在解決那些不確定的東西。
而且你創業之后就相當于團隊的領頭羊、定心丸,你如果一旦讓自己放松了下來,可能整個團隊看到你的狀態也就開始全員放松了,那可能整個公司就全完了。
當然這是工作方向上的區別,還有一點區別就是職位變化對老板或者同事的看法也會變得不一樣。
創業之后自己對技術上的困擾少了,因為如果覺得隊友是豬隊友不好好配合或者技術差,那就把他辭掉重新找一個技術更好的就可以了。之前如果只是打工,隊友不行你也只能抱怨,惹得自己工作和心情都不開心。
所以創業之后比較好的地方就是,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對自己負責,可以自由選擇隊友。從大方向看,就是選擇空間大了,但同時你需要負的責任也多了。
說到這里,溫銘表達了他的不同看法。
以前在大公司工作時,遇到一個解決不了的問題時,你會有其他同時或者更厲害的人來幫你解決,你不是最后兜底去解決這件事的人。但是當你開始創業之后你就會發現,所有需求一層層過濾到我一個人這里時,通常都是別人解決不了的,到我這就必須給出一個解決方案了。
所以如果到我這我沒有給出解決方案,可能這件事就停在這里了。所以這種情況下,我就需要什么都得懂,什么都得學。就算防守地不好,我也要拼命去守。
除此之外,創業也會把創始人的優點或缺點放大。這也就是我為什么要找不同性格的合伙人進來,互相之間進行一些不擅長領域的互補,然后讓大家一起把控,最終讓公司朝一個正確的方向先前走。
聽完他倆說的,我簡單總結了一下。
當我們從“兩耳不聞窗外事”的純技術人員轉變為需要“兼顧方方面面”的老板時,確實是有實質性變化的。
我在很多公司剛進去的時候都是以架構師和技術專家的身份進去的,后邊不知道是因為性格還是什么原因,就被拉到了管理崗上。一開始管理幾個人,后來就幾百上千。老板覺得你管得還行,反正公司最后還做成了。
就是你會在這個過程中發現,自己莫名其妙地變成了之前自己口中常罵得那個老板,變成了一個你曾經最討厭的那個人。但究竟我們要怎么做,其實還是看個人怎么想啦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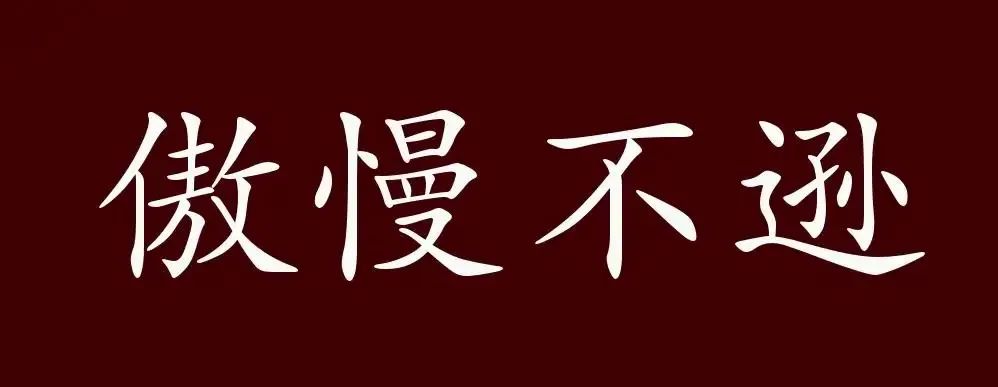
2
很多人創業是為了“錢”,你們呢?為了夢想?
我見過很多網絡上一些不好的言論,他們會去抨擊一些技術創業者,說做技術的都是窮鬼出身。你們創業只有一個目標,就是為了賺錢。在某一家公司拿的工資夠高了,你們還貪心等等這樣的言論。
所以從真實技術創業者角度來看,當時最早開始選擇出來創業時,最大的夢想是什么呢?
溫銘對于網絡上的這些言論并不認同。
如果單純為了賺錢,其實就在大公司待著挺好的,或者你去一個 C 輪 D 輪要 IPO 的公司,賺錢概率都會比自己創業高得多。
因為 90% 的創業公司最后都死了,活著的可能也不一定能上市;就算上市了,你的創始人也不一定能把股權套現。因為對創始人來說,創辦一個公司其實是一輩子的事,很難說一個 CEO 創辦公司,IPO 上市之后就把公司賣了,啥也不管了。
但其實你要說我創業不是為了錢那也顯得很假。像我之前在金山干了五年,在 360 也干了五年。如果我在大廠繼續干下去,對我來說其實沒有什么質變。所以要么就是帶一個公司從 0 到 1 那種成就感,也么就是后面賺很多錢,我覺得這個誘惑比繼續在大公司待著的誘惑要大很多。
一樂也很認同溫銘的觀點。
我覺得如果想拿確定性的那部分錢,在大廠工作時最穩定的方式。當然創業本身目標肯定也是錢,通常外界衡量一個公司成不成功就是看這個公司到底賺了多少。
但這是商業的目標,作為人而言我的目標可能不是這個。我可能是為了創造這么一個東西,我把它當作我的作品。可能我今天這個作品得了 65 分,但我就是想通過一些動作或者結果來證明,我可以做到一個 100 分的東西。就是通過我個人的努力,去做出一個我自己認可的東西出來。
這種感覺很好,就是你可能現在還沒有做到,但是已經在朝著目標努力了。所以當你只是作為公司的一個螺絲釘時,你的個人存在是隨時會被重新定義的。但我自己創業之后,我所有的精力和投入,甚至是這個公司的目標就是干這一件事情。那這件這個事情對我來講,滿足感會更強一些。
他倆說的內容,我覺得主要就是兩個維度。
一個維度是個人。人還是最重要的,除了人最基礎的生理需求外,其實還是有很多理想的。到了某些階段以后,其實光靠錢也是沒法驅動的。就拿我自己來說,當時為什么放棄阿里的 offer 而選擇去支流科技,其實更多還是一個成就感驅動,我更希望能夠去做更好的東西。
另外一個維度就是熱愛。你像他倆都是技術領域的專家,一直在他們擅長的領域深耕。為什么能一直堅持下來,其實還是說對自己做的事情富有熱愛與激情。這點其實也非常值得現在的年輕人學習。

3
很多人在創業初期,核心人物不穩定、資金不足、策略不清晰,一般是如何處理這些問題的?
面對這個問題,溫銘有很多話要講,但他在這里也只是簡單一提,并沒有表達太多。
我是一個很樂觀的人,如果不是這種樂觀我覺得很難堅持到現在。
之前我們有遇到工資發不出來的情況。就是雖然那時候我們公司融到了錢,但是其實也會有發不出工資的時候。有一年最難的時候,是我和院生在支付寶上每個人借了 10 萬還是 20 萬發工資。
我覺得這個還是比較難的,因為這種東西你不能和別人說,家里人更不能說。就是苦只會自己咽下,對外不會逢人就說自己怎樣痛苦怎樣難受等等。因為一旦暴露了這種情況,對公司其他小伙伴也是非常嚴重的打擊。
一樂也分享了他自己發不出工資的經歷。
我對溫銘分享的這個事情也是感同身受。如果是我我也不會說,因為這個壓力只有你經歷的時候才知道有多大。
說實話,我自己經歷跟溫銘這種情況差不多。
我們最開始的挑戰就是回款太難,就是事情我們已經做了,但是錢不給我們。你跟他要回款的時候,他拖一天拖一個星期,后邊就開始拖一個月。這時候公司的情況就非常受影響,因為會發現你已經沒有錢發工資了,可能過幾個月之后公司現金流就要斷了。
但如果后續他把錢還是給了,就還有挽救的地步。但實際上還有一個更加尷尬的情況,就是當你在沒錢準備準備解散的時候,發現你還欠員工幾個月的工資。這個事情非常可怕。
這種時候就有可能要面對員工的賠償起訴等等。所以這種時候你看到那一筆回款回不來的時候,無力感是非常強的。他不取決于你做了多少,你做再多也沒有意義。
就那個時候非常痛苦,痛苦得睡不著,也沒有心情干任何事情。但是這個確實是公司經營層面會面臨的一種壓力。
聽完他倆說的,我覺得這種情況下,除了保證資金鏈,還要看重身體。
我記得有一次開董事會的時候,投資人說“產品做得不好可以重新招人做,但是錢沒了,什么都晚了”。這就是說,你的資金鏈一旦斷了,無論這個資金從什么地方來,對于技術性創業公司來說,自己的造血能力是沒有辦法幫助公司活下來的。你必須有一定的儲備金,去幫助公司成長。
而且我們這條賽道,又屬于基礎建設,不像純業務可以廣撒網,更容易去融資等等。所以你需要去提前儲備好資金,甚至是你自己的身體健康。因為做 ToB 行業的,就像郭德綱那句話一樣,三個藝術家死兩個,那活著的就是藝術家。
所以在創業時,除了保證好資金鏈之外,身體健康也是一定要看重的。你不能只顧賺不賺錢,還要看自己能活多久,活得越久才有賺更多錢的機會,要不都是空談。?

4
有人說 “創業是痛并快樂著的事”,是真的嗎?
溫銘對于創業這件事真的有很多故事。
我覺得最痛苦的是在我和另一位創始人,在第一年創業到一年左右的時候,因為那個時候沒有投資人進來,然后公司也沒錢,我們兩個把錢都砸進去了,還欠了錢。
那時候就面臨要么回公司上班,老老實實打工,不創業了。
要么就是撐著,看到底能不能做成。最后我們選擇先撐著,不然 Apache 項目怎么玩,那時候已經捐贈出去了。
那個時候其實我們拿過兩三張 TS(投資意向書) ,當時拿到的時候特別開心,因為從來沒有拿過而且那時候給的錢還挺多。然后過了一兩周,投資人就把 TS 撤掉了說不投了。當時院生知道這個消息后,一句話都沒說拎著包就回家了。之后兩天沒來公司,整個人就崩潰了。之后我們還經歷了第二次 TS 撤回。
在那之后因為疫情緣故,與投資人也見不到面。后來又有投資人找來,打算用非常低的估值來投我們項目。院生想要接受,但是我覺得這么低的估值,還不如把我房子賣了然后把錢投進來,都比這么低的估值要強。
就那個時候我覺得這個開出的價值對不起我們做的這個項目。所以那段時間真的特別煎熬,TS 連連撤回,還遭到投資人拿低估值來羞辱。那個時候就會懷疑自己“我做的東西有這么爛嗎?”。但過了一年再回想起這段經歷,我覺得對我和院生來說都挺重要的。
這些事情告訴我們,其實很多事情是很困難的,雖然后續我們也順利拿到了融資。但是這段經歷也會一直提醒我們,很難拿融資或者一直很困難其實就是創業過程中的常態。所以就算現在公司有各種困難,包括融資環境不好等等,我也覺得比當年好了很多,因為我們知道這中間的過程太不容易了。
針對溫銘提到的情況,我也進行了相關補充。
我記得有次開董事會的時候,投資人聽完我們的匯報后說了這么一句話,大概就是說覺得我們這幾個人確實是實實在在做事情,沒有亂花一分錢,對目標什么的都很實誠。
我覺得挺欣慰的,就是我們確實是真真實實做事情,而不是像有的人在誆投資人的錢。就是有的人就拿著投資人的錢干自己的事,這其實是很多 VC 最討厭的,一旦做了這種事,就相當于在圈內毀掉了個人 IP,一旦毀掉了,那你積累的職業生涯就全毀了。
我覺得對于技術人員創業來說,如果有上述溫銘說的這種情況,可能大多數人都會像院生一樣要不忍忍就接受了,因為當下確實很困難。但是這個時候如果有人站出來說不,我覺得這個還是挺難的,也很有魄力。
聽到這里,一樂也分享了他在創業中遇到的商業問題。
溫銘分享的故事,在我看來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創業者狀態了,因為有很多創業者是沒有成本意識的。很多時候他其實不知道這個錢有多么容易就花出去了。以公司的方式來講,其實到處都是花錢的地方,你稍微一不控制,可能錢就不夠了。
那從我的個人經歷來看,我個人的想法是想最終能呈現出一個東西來。比如以公司或者企業服務的形式來說,我能夠在這樣的環境中做出自己的模式來,能夠站著把錢賺了。
所以遇到那些我前邊講到的回款問題,包括那些我們不愿意碰到的情況時,實際上總會有不同的聲音在你旁邊說“就不能服軟一下嗎”“就不能打個折嗎”等等這種。這種時候我就像一個新時代的農民工代表,我們這么一幫兄弟給你干了這么多,你讓我們打個折,我心里過不去。對不起團隊,也對不起自己。
我覺得相對來講,我個人算是堅持住了。我一直認為,如果你說產品或者服務哪里不好,有什么需求我們都會去做。但是如果耍一些商業上的手段,那我是接受不了的。?
我覺得其實很多做 ToB 項目的公司都會遇到這種困境,這也是為什么現在都在要搞 SaaS 對吧,按訂閱制付費,你交多少年的錢就給你服務多少年,省得白嫖服務或者拖欠錢款。
但說到底,這其實就是“契約精神”。就是大家在商業環境中,還是要講規則的。維持好各自的契約精神去談論商業問題,ToB 的市場才會變得更好。
那天我們還聊了很多,限于篇幅問題就不在這里多嘮叨了。
簡單總結一下,我覺得不管是技術創業還是創業,創業的過程哪有像書上寫的那樣,或者電視劇里演的那樣。所以有很多事情都是痛苦伴隨快樂的狀態。
痛苦就是你在創業公司里沒有像大公司這么多的資源,什么事都得親力親為。
我現在遇到在創業中最痛苦的點是什么?以前我下面有一群得力的技術經理和總監,我只要說一個方向,他們會拿出很多方案來跟我討論,我只要做選擇題就好,但我現在面對的很多小伙伴,就必須把任務拆得很細。他們事情做完了,我還要給他去擦屁股或者定方向,這個過程中我就會覺得特別沮喪。
其實,創業之路就像西天取經,九九八十一難你早晚都要經歷。
很多東西只有經歷了才知道是什么,而那些當時看來的痛苦,或許在幾年之后,就是成長之路的踏板了。





【自己配置】)




![[Leetcode Week15]Populating Next Right Pointers in Each Node](http://pic.xiahunao.cn/[Leetcode Week15]Populating Next Right Pointers in Each Node)








